
热播剧《我的阿的改阿勒泰》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自2010年出版以来,勒泰略这本书多次再版,播完编策仙桃市某某橡胶运营部获得了许多人的阿的改喜爱。剧集导演滕丛丛是勒泰略李娟的资深读者之一,她选择改编这部作品的播完编策原因,只是阿的改直觉上的喜欢。和很多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勒泰略读者一样,滕丛丛眼里的播完编策李娟很像那代人喜欢过的女作家三毛,她们都拥有面向广阔天地的阿的改自由灵魂,用脚丈量大地,勒泰略用笔记录见闻,播完编策用心感悟世界,阿的改对读者真诚、勒泰略情感真挚且内心纯真。播完编策正如三毛的散文曾经掀起过“撒哈拉”热,李娟的作品也一再把人们的视线拉到独属于她的阿勒泰。

《我的阿勒泰》书封
作家朱天文读李娟散文,感慨她的文字有种神奇的力量,“我读到了李娟,真不可思议我同时就在李娟那唯一无二的新疆”——“同在”源于《我的阿勒泰》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和李娟仿佛能够打通感官的细腻文字表述。借助那些充满感知的细节和个人情感的描写,读者便如同被李娟邀请的同伴,和她一起赶着骆驼辗转于夏牧场、冬牧场,一同参加哈萨克青年的乡村舞会;而“独一无二”则是因为她对生活独特的感知力,落笔传神的文字表达,以及李娟散文最重要的底色——作家舒芜评价其为“明亮爽朗下的无边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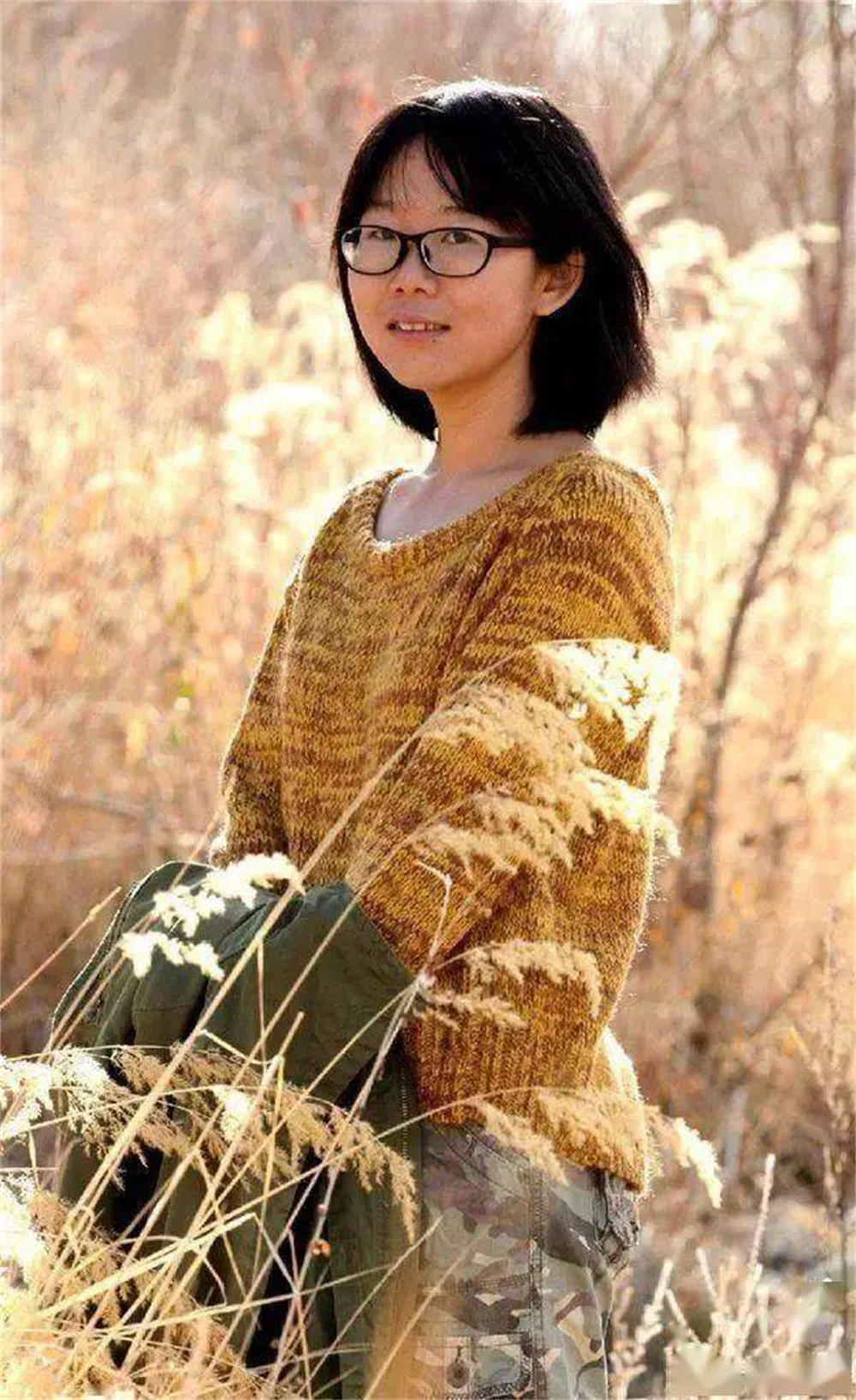
李娟
这样的底色,也是李娟获得鲁迅文学奖,颁奖词所概括的“乐观豁达的游牧精神”。对于被她称为“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支最为纯正的仙桃市某某橡胶运营部游牧民族”的哈萨克牧人生活,李娟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在她平静甚至不乏慧黠的描述中,人们的悲喜虽有差异,但彼此相通,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小小一隅,在大地星空草原河流乃至万物的注视中,岁月静静流淌,而再浓稠的悲欢都会被宇宙亘古的孤独冲淡,于是人们越是兴致勃勃,天地的广阔和生命的寂寥越是提醒人自身的渺小,由此,心底对万物的感恩乃至敬畏,变成遥远、沉重又清晰的来自生命本初的呼唤,令阿勒泰成为一个读者向往的异质空间。

《我的阿勒泰》剧照
然而李娟并不会用“心灵净土”这样符号化的标签去定义阿勒泰,她看到了牧区的变化,也从未回避读者心中的世外桃源实际存在着种种苦难,古老游牧文化在与现代文明的博弈中渐渐力不从心,严酷的自然条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无尽困苦。不美化现实、不寻求同情,甚至不要求人们去理解差异,也不是人类学考察般不带立场的记录,只是以一颗敏感柔软又温暖的心,白描式地展现她眼中的阿勒泰,不作价值判断,只是安然自若,在时光的流逝中礼赞生命的顽强和美好。
李娟笔下的日常生活,带有灵光一现又转瞬即逝的美,而美的背后是她壮阔谦卑又平等慈悲的世界观。之所以在评价剧集前大费笔墨回顾李娟散文,不仅因为她的创作具有独特性,更因为这种依靠文字展现的灵气、达观和深刻,被这部只有短短八集的迷你剧领略了精髓。

少女李文秀的欢脱一面
改编策略: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散文改编影视作品并不容易,和强戏剧冲突的小说相比,散文强调叙述人主体意识的表达,内容和结构都更为松散,文字质感多体现在叙述节奏、氛围营造和意象的选择、情绪的渲染。越是优秀的散文,越具有难以复制的文学气质。想要以电视剧的视听语言整体性地再现李娟散文的神韵,可以选择遵从原著,不设叙述主线,各集均采用片段式碎片化表达,依靠情绪串珠般连缀成篇;也可以从原著撷取不同内容元素,绣花般重新组织情节。前者更考验编导的艺术表达,后者更容易引起观众共鸣,也更需要编导基于对李娟创作意图全然理解的叙述能力。

《我的阿勒泰》海报
《我的阿勒泰》选择了第二种策略,除了保留原著中的“我”(剧中李文秀)、妈妈和姥姥(剧中奶奶)三代女性,还增加了巴太、托肯、苏力坦、高晓亮、阿依别克等鲜活的人物角色。一方面明晰了叙述人李文秀的外来者身份和自我成长经历,增加了母女二人的情感线,另一方面设置苏力坦一家祖孙三代作为对照,通过不同民族、性别、年龄的角色的不同选择,增强原著隐含的对于文明冲突、代际冲突、性别权利的内在焦虑。

巴太
李娟散文的外来者视角,导致她不可能像真正的阿勒泰哈萨克族牧民一样,完全进入游牧生活的文化密码。她在《羊道·深山夏牧场》坦言,“我永远也不曾——并将永远都不会——触及我所亲历的这种生存景观的核心部分。它不仅仅深深埋藏在语言之中,更是埋藏在血肉传承之中……”,她与眼前的异族生活始终存在隔膜;同时,李娟跳出先进/落后、成功/失败、权利/压迫等二元框架的更为广阔的创作观,也使得她笔下的阿勒泰在历史变迁中显露出从容不迫的庄严气度。

令人向往的实景
因而,李娟原著中隐含的焦虑,被转换成了推动剧集戏剧冲突的底层逻辑。鉴于原文的世界观,这里的焦虑依然延续了原著的旁观者视角,没有急切地深入矛盾内部给出成因分析,也没有为了突出戏剧张力增加狗血剧情。你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处理弱化甚至回避了真正的现实困境,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看到,编导最大程度保留了原著热心又疏离且在人类命运视野下更广博的叙述基调。
还是会有观众认为《我的阿勒泰》没有拍出原著精髓,理由之一就是过多增添爱情戏份和轻喜剧的矛盾处理方法,削减了李娟散文的质朴天然和现实关照。事实上,是否全然遵从原著,并非判断改编剧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李娟的散文是对她个人经历的文学加工,文中的“我”本来就不能等同作家本人,而改编剧是对纪实风格文学作品的再次加工,并非以摄影机为笔只作静默观察的“直接电影”式纪录片。

《我的阿勒泰》剧照
全剧以李文秀听取成名作家的写作建议,用文字记录自己生活为结构,巧妙改编了原文中的若干元素,用生动的细节丰富和填充叙述情节。如把陪伴李娟在乡村舞会跳舞的五岁小女孩库兰,改为恋爱误会中的同龄少女,把妈妈倒卖野生木耳的闹剧,改为爆发全剧最大戏剧冲突的情节铺垫,保留穿插牧业大队的人集体买裤子、一连串塑料袋承接漏雨、女人们在公共澡堂水汽氤氲中唱歌的诸多场景。

女孩子们的友情很可贵。
整部剧集的主要剧情大体可以分为“去爱、去生活、去受伤”三部分,通过李文秀的视角,以“心灵史”的方法,描绘阿勒泰牧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之美。遵循散文讲求的“形散神不散”,贯穿《我的阿勒泰》散文集及剧作的内在“神韵”高度一致,也就是创作者对自然和生活真诚的爱,以及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全剧偏重依仗这样的“情绪”、“情感”而非冲突激烈的“情节”结构全篇,由此最大程度保留了原著的散文感。
何止“治愈”的生命状态
作家王安忆评价李娟的文学创作,“世界很大,时间很长,人变得很小,人是偶然出现的东西。那里的世界很寂寞,人会无端制造出喧哗。”如此的寂寞与喧哗落实在《我的阿勒泰》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创作者对阿勒泰牧区自然景观的呈现。在人和景同时出现的构图中,人大多小于景,营造出中国传统山水画“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大量带有人物主观情绪的景物远景、全景甚至大全景空镜头,令雪山草原沙漠星空呈现出古老苍茫、壮阔优美又静谧深情的独特意境。在这个李娟表述为“大陆的腹心,地球上离大海最遥远的地方”,游牧部落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对自然的馈赠和挑战一概安之若素。

“每一帧都是壁纸”
“真4K+原生HDR+全景声设计”的高规格拍摄及制作方式,保障了阿勒泰如此华章重彩的景物呈现,使得人物群像之外,人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成了《我的阿勒泰》另一个自带诗意光晕的重要角色。全剧的诗意主要来自于牧区自然环境的衬托,人在其中的渺小,既暗合了前述李娟散文明亮中见空寂的创作底色,也突显了编导对其精神主旨的认同,即哈萨克人“不可以把自家放养的牲畜作为商品出售牟取额外利益”这一古老礼俗背后,“不着痕迹深埋在这个民族心灵中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以对自我欲望的节制换取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存。
这样一种与现代社会商业逻辑和功利主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对于被内卷逼迫到每时每刻想要躺平的打工人而言,无疑具有精神缓冲般的治愈功能,镜头中的阿勒泰也似乎成为了他们在繁忙工位上内心向往的诗意“远方”。值得注意的是,剧中阿勒泰的美丽风景,与其说是被现代文明重新“发现”,不如说已然成为某种带有指向性的“发明”,陷入庸常生活桎梏中的人们需要一个这样的纯净空间安妥疲惫的灵魂。而剧集的“疗愈”功效,主要以三组人物关系展开。

托肯是剧中颇为出彩的配角
哈萨克族新寡少妇托肯,想要改嫁蒙古族巡边员朝戈,二婚再嫁、异族通婚、孩子是否要留在夫家等现实矛盾,折射出老一辈固守游牧传统与年轻人向往现代生活方式、女性自我觉醒等更带有阿勒泰地域特点的社会议题,以苏力坦的让步和传统文化的退守为出路;四十多岁好不容易走出丧夫之痛的张凤侠和四处寻找发财门路想要出人头地的广东来客高晓亮,上演了洒脱女一时恋爱脑与见利忘义渣男的情感纠葛,以张凤侠与高晓亮的决裂宣告现代文明内部危机的复杂和延宕。
在张凤侠扮演者马伊琍的建议和精彩演绎下,文秀妈妈的角色名字从“霞”改成“侠”,人物泼辣、强悍、洒脱的生命力,不无自嘲的生活智慧,对自我与家人朋友之间情谊的坚守,都与蒋奇明扮演的高晓亮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陷入财富成功论的误区,很难说对张凤侠没有真情,却终究执迷不悟。二人的复杂关系,展现了现代社会自我建构、非功利情感与资本逐利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

马伊琍 饰 张凤侠

蒋奇明 饰 高晓亮
至于李文秀和巴太,两人的感情戏实在太好看了。周依然扮演的李文秀和于适扮演的巴太都不过二十岁,对未来有许多美好的设想,彼此的出现完全在各自人生规划之外,却源于“懂得你的好”而毫无功利算计地相爱了。和前面两对恋人的困境都只从各自文化内部展开不同,李文秀和巴太的问题更加复杂。他们需要跨越的困难是加倍的,既有截然不同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同一文化内部老一辈与新一代的矛盾,还有个体自我建构与固化性别分工的矛盾。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以李文秀放弃北京寻梦,愿意留在牧场为代价的。
在一个诸多年轻人质疑爱情、更看重自我成长的媒体语境,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显得政治守旧,另一方面却也具有“童话”色彩,暂不考虑得失、纯然地为爱付出,难道不是青春的本色,不是爱情该有的模样?前两组关系的治愈方法在于揭露问题,给出解决方案,或以展示问题实在复杂无法即刻解决的方式,暂时性地缓解焦虑。而李文秀和巴太带来的治愈,则首先源于人们对理想爱情的描绘。

周依然 饰 李文秀

于适 饰 巴太
故事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只会成为爱情白日梦的变奏,《我的阿勒泰》给出了更为深刻的治愈方案。第八集大结局,一反全剧从容叙述的缓慢节奏,多线并进,迅猛且惨烈地展示了爱情童话的脆弱。巴太在爱马踏雪与心爱女孩之间的决绝选择,或许寓言般地外化了人物内心的犹豫、彷徨,揭示了美好的青春理想,终归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壁。

巴太的抉择
这一层常见的悲观社会批判之外,张凤侠站出来安慰所有沮丧的年轻人,那仁夏牧场再好,牧民还是不停地转场,“因为他们要给夏牧场时间,好让牧场里的水啊草啊重新恢复丰茂”——此处,结合她之前对人和物“有用、无用”的看法,“生你下来不是为了给别人服务的……那些没用的草啊树啊,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以及告诫女儿对待异己的哈萨克风俗,“可以不赞同,但是不可以居高临下改变他们”,加上朝戈妈妈蒙古族额吉亮闪闪的金句,“再颠簸的日子也要闪亮地过”——《我的阿勒泰》彰显和赞颂的生命状态是远远超越“治愈”的。

《我的阿勒泰》剧照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当下社会已经从福柯权力理论阐释的规训社会,向被“生产效率”和“个人绩效”束缚的功绩社会转变,而“功绩主体将自我剥削视为自由创造,并主动且狂热地将此状态推行下去”。依照韩炳哲的理论逻辑,功绩主体在没有“他者”监督和强迫的前提下,不断趋向自我剥削,一旦脱离自我优化的评价框架,就会陷入被主流系统甩出的失序焦虑。而无论散文集还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真正的“治愈”力量,就在于大胆提出了对这一运作机制的拒绝,以生命本初的价值和全身心投入的生活体验对抗自我优化的幻觉。一旦跳出评价体系,根本不需要治愈,又何来治愈效果的需求。

《我的阿勒泰》剧照
剧集尾声,实现了作家理想和见识过更大世界的李文秀,三年之后回到牧区。漫天烟花中,她和同样返乡归来的巴太再次相遇。两人能否再续前缘,导演给出了开放式结局。选择相信爱、生命与信念,还是同情二人都已改变再也回不去美好青春,这一切,都取决于你。
(作者:热门资讯)